- 相關推薦
中國歷史人物簡介:惠施
惠子(約前370年—前310年),名施,華夏族,戰國中期宋國(今河南商丘)人。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學家,是名家學派的開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惠施是合縱抗秦的最主要的組織人和支持者,他主張魏國、齊國和楚國聯合起來對抗秦國,并建議齊、魏互尊為王。后又為伐齊存燕使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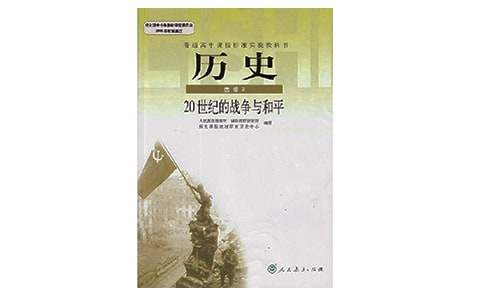
人物生平
主要在魏國生活的惠施學識很淵博,魏惠王十分贊賞他的博學,經常聽他講學,還十分器重他,拿他與管仲相比。當然,惠施對魏王也很忠誠,作為合縱抗秦的倡導者,他在各國享有很高的聲譽,因此,常被魏惠王派到其他各國處理一些外交事務。
張儀來到魏國后,打算為秦連橫,一起進攻齊楚。惠施因與其政見不合被迫離開了魏國。
他先到楚國,又回到家鄉宋國,在那里遇見并結識了莊子,與之交游甚好。后來魏惠王離世,張儀失寵離開,他又得以重回魏國。
惠施為魏國制定了很多法律,但因其著作散失,這些都沒能流傳下來。《莊子·天下篇》用“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來形容惠施的知識淵博,藏書也很多。成語“學富五車”便是由此而來。
惠施十分善辯,常與莊子討論問題,其中,濠上觀魚的故事,就是兩人的著名辯論。
莊子與惠施交游于濠水的橋上,看見水中魚兒悠然戲水,便說道:“你看魚兒在水中多么快樂呀!”
惠施反駁道:“你又不是魚,怎么知道魚快不快樂?”
莊子回答說:“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魚快不快樂?”
惠施很機敏,立刻利用莊子的邏輯反駁莊子:“我不是你,當然不會知道你的想法,但是有一點很清楚:你也不是魚,所以你也不可能知道魚是否快樂。我們沒必要再爭論下去了!”
辯論到這里,莊子本已無話可說,因為惠施用的正是莊子的論據。然而,莊子突然話鋒一轉道:“那我們就再回到剛才的對話,你問我,‘你怎么知道魚快不快樂?’既然你這樣問了,你便是已經知道我知道魚是快樂的了,否則怎么會這樣問呢?那么,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是在這濠水橋上知道的!”
這則故事被記載在《莊子·秋水篇》里。惠施死后,莊子曾感慨世上再無可言之人……惠施主張廣泛地分析世界上的事物,認為在廣袤無垠的宇宙里,任何時間、空間上的差異都是微不足道的,萬物的相同和相異都是相對的,是在不斷變化的,看似相異的對立之中有著同一性,這便是“合同異”。
為此,惠施提出了“歷物十事”等命題來進行論證。《莊子·天下篇》記載了這十個論題,后世稱之為“惠施十事”。比較著名的有:“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惠施說的“萬物畢同畢異”,是指萬物各有一個“自相”,例如一胎里生不出兩個完全一樣的兄弟;一棵樹上開不出兩朵完全一樣的花;一朵花上找不出兩片完全一樣的花瓣……這便是萬物的“自相”。
有自相,所以“萬物畢異”,但萬物卻又都有一些“共相”。
例如男女有別,卻同是人;人與禽獸有別,卻同是動物;動物與植物雖有別,卻同是生物……這便是萬物的“共相”。有共相,所以“萬物畢同”。
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惠施的這一思想與莊子“齊萬物為一”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
從整個名辯思潮的發展來看,惠施與一般只著眼于社會政治倫理問題研究和只停留于思維形式研究的諸家不同,他是先秦時期注重研究自然,頗具科學精神的一位思想家。他注重從事物的聯系和發展來看待事物的差異,發現差異的相對性,這對當時以靜止觀點看待實物的形而上學思想是不小的沖擊,在中國古代哲學上具有積極的進步意義。但他過分夸大了事物的同一性,忽視了個體的差別和相對穩定性,因而又走向了哲學的另一個極端—相對主義的錯誤。[1]
《戰國策》是這樣記載的:
張儀逐惠施于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者來,而惡王之交于張儀,惠子心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棄所貴于讎人,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于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惠施是戰國時的名士。《戰國策·魏二》、《韓非子.說林上》記載說,惠施的友人田需一度受到魏王的器重和寵用,惠施于是告誡他說:“你一定要很好地對待魏王身邊的人。比如那楊樹,橫著栽下能生存,倒著栽下能生存,折斷栽下它也能生存。但是如果十個人栽它而一個人拔它,那它就難以生存了。十個人栽這一易生之物,卻抵不過一個人的破壞,原因就在于栽起來困難,而拔除它很容易。你今天雖然能使自己受器重于君王,但如果想要除掉你的人多了,你必定就很危險。”
田需受到魏王的器重,一定具有他取得魏王器重和賞識的某方面能力。然而,不管田需的個人能力有多大,都不能必然地保證他長久地受到君王器重,因為魏王作為一國君主,他處在國家政治活動圈的中心,受到許多公侯大臣和左右侍臣的拱圍,他必有自己身邊的一批親信之人,這些人物參與他的決策和用人,影響他對事物的判斷,甚至會動搖他的某些既成觀念,田需如果不能爭取到這批人物的認可和支持,那他們必然要在魏王面前詆毀田需,最后勢必動搖魏王對田需的信任,使田需失去已經獲得的寵信地位。
楊樹是一種易生之物,但它一經栽下,卻經不起一人的拔除,要想使它生存下去,就必須戒除任何人的拔除。同樣,田需雖有贏得君王重用的能力,但他也經不起人們的詆毀,要想取得君王的長久信任,也必須防止人們在君王面前的詆毀。惠施把這一道理明白地告訴了田需,從而教給了他一種實用的保寵之方。
惠施的保寵之方向人們無意間透露了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它告訴人們,一個人在社會上受器重的程度,不僅取決于他的個人能力,而且取決于他與周圍世界的人際關系,取決于他聯系大眾的程度。良好的人際關系能夠保證個人的潛在能力得以在社會上實現。
惠子死后葬于現的滑縣八里營鄉冢上村,占地4000平方米,高于地面30多米。后人稱之謂惠子冢。冢內建有磚砌墓,外用土封,上建三宮殿、琉璃殿、鐘樓、鼓樓等,民國年間全部拆掉。冢下為龍山文化遺址,目前保護較好,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思想體系
文學
《莊子·天下》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是說他知識淵博,書也很多。有個名叫黃繚的人問惠施"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他不假思索,隨口回答,說得頭頭是道,可惜他的著作早已失傳,否則當是最有價值的科學遺產。《莊子》保存了惠施的"歷物十事",②即分析物理的10 個命題。《荀子》、《韓非子》和《呂氏春秋》等書也保存了一些惠施著作的片斷。我們分析惠施的思想,主要是根據《莊子·天下》的"歷物十事"。
惠施的"歷物十事"貫穿著"合同異"的思想,他是名家"合同異"派的代表人物。他說:"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這里是指事物本身的同一與差別的相對性。"大同"和"小同"有差異,這就叫"小同異";萬物都相同又都不同,這就叫"大同異"。什么是"大同"呢?比如馬;凡是屬于馬這一類動物都包括在內,這就是"大同"。其中黑馬、白馬、大馬、小馬等等又有差別,這叫著"小同"。馬這個大類概念與黑馬、白馬這些小類的概念有差別。如果從相同的方面看,這些都是馬。由此可以推知,萬物都有相同的一面。如果從不同的方面看,這些馬又都有差異。由此可以推知,萬物都有不同的一面。惠施對事物的統一和差別的相互關系,有一定的認識。他認為事物都有相同之處,同時又有差別。事物的相同和差別是相對的,它們同處于統一體之中。然而惠施特別強調事物的差別是相對的,相同才是絕對的,所以他得出萬物"畢同"的結論。這樣就把相同的事物和不同的事物都抽象地統一起來。他更進一步推論出:"氾愛萬物,天地一體"的結論。《呂氏春秋》說:"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①這是對惠施"氾愛萬物,天地一體"的解釋,這已與莊子的"萬物皆一也"②很接近了。但是,惠施的思想與莊子的相對主義還不能等同。莊子的相對主義否認事物之間有質的差別,實際上是否定了事物的客觀存在。惠施并沒有完全走入這樣的主觀主義。惠施對"大同異"、"小同異"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分析,看到了其間的變異,只有這樣分析,才能如實反映客觀事物。而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又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主張"合同異"的惠施,也不可能絕對不講"離"。同樣道理,主張"離堅白"的公孫龍,也不可能絕對不講"合"。不過,惠施雖然講"離",但最終還是講"合",而公孫龍雖然講"合",但最終還是講"離"。由此可見,惠施著重在概念外延的擴大,而公孫龍則著重在內涵的分離。這樣看來,"合同異"、"離堅白"兩派的名稱還是符合惠施、公孫龍思想實際的。
惠施的"歷物十事"研究的對象是物質世界。他善于對物質世界的本質和規律作出哲學的概括。在"名"、"實"關系上,他是從現實存在出發的,承認"實"是第一性的,而"名"是"實"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他和公孫龍的詭辯是有所區別的。
哲學
惠施和鄧析、公孫龍一樣,是名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和墨家一樣,曾努力鉆研宇宙間萬物構成的原因。據說,南方有個奇人叫黃繚的,曾詢問天地不塌不陷落以及風雨雷霆發生的原因,惠施不假思索,立刻應對,“遍為萬物說”(《莊子·天下篇》)。莊子曾說惠施“以堅白鳴”(《莊子·德充符篇》),批評惠施“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莊子·齊物篇》)。可知惠施的論題,主要的還是有關宇宙萬物的學說。他的著作已經失傳,只有《莊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個命題。
惠施的十個命題,主要是對自然界的分析,其中有些含有辯證的因素。他說:“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大一”是說整個空間大到無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說物質最小的單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內部。
這和后期墨家一樣認為物質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物質所構成。萬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質構成,同樣基于“小一”,所以說“萬物畢同”;但是由“小一”構成的萬物形態千變萬化,在“大一”中所處的位置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以說“萬物畢異”。在萬物千變萬化的形態中,有“畢同”和“畢異”的“大同異”,也還有事物之間一般的同異,就是“小同異”。他把事物的異同看作相對的,但又是統一在一起的,這里包含有辯證的因素。
惠施有些命題是和后期墨家爭論的。后期墨家運用數學和物理學的常識,對物體的外表形式及其測算方式作了分析,下了定義。 《墨子·經上》曾說:“厚,有所大。”認為有“厚”才能有體積,才能有物體的“大”。而惠施反駁說:“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認為物質(“小一”)不累積成厚度,就沒有體積;但是物質所構成平面的面積,是可以無限大的。后期墨家曾經嚴格區分空間的“有窮”和“無窮”,《墨子·經說下》說:“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認為個別區域前不容一線之地,這是“有窮”;與此相反,空間無邊無際,這是“無窮”。而惠施反駁說,“南方無窮而有窮”,就是說南方盡管是無窮的,但是最后還是有終極的地方。后期墨家認為“中”(中心點)到相對的兩邊的終點是“同長”的。《墨子·經上》說:“中,同長也。”而惠施反駁說:“我知天下之中央,燕(當時最北的諸侯國)之北,越(當時最南的諸侯國)之南是也。”因為空間無邊無際,無限大,到處都可以成為中心。后期墨家認為同樣高度叫做“平”,《墨子·經上》說:“平,同高也。”而惠施反駁說:“天與地卑(“卑”是接近的意思),山與澤平。”因為測量的人站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高低就不一樣。站在遠處看,天和地幾乎是接近的;站在山頂上的湖泊邊沿看,山和澤是平的。
惠施把一切事物看作處于變動之中,例如說:“日方中方睨(“睨”是側斜的意思),物方生方死。”太陽剛升到正中,同時就開始西斜了;一件東西剛生下來,同時又走向死亡了。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事物矛盾運動的辯證過程。但是他無條件地承認“亦彼亦此”,只講轉化而不講轉化的條件,這樣就否定了事物的質的相對穩定性,不免陷入到相對主義的泥坑中去。
歷物十事
惠施和鄧析、公孫龍一樣,是名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莊子·天下篇》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是說他知識淵博,閱覽豐富。南方有個奇人名叫黃繚,詢問惠施“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假思索,應對如流,“遍為萬物說”。莊子曾說惠施“以堅白鳴”(《莊子·德充符篇》),批評惠施“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莊子·齊物篇》)。可知惠施的論題,主要是有關宇宙萬物的學說。可惜他的著作已經失傳,只有《莊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個命題,即“歷物十事”:
(一)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二)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三)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四)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五)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六)南方無窮而有窮。
(七)今日適越而昔來。
(八)連環可解也。
(九)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
(十)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惠施是名家“合同異”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歷物十事”雖然主要是對自然界的分析,卻貫穿著“合同異”的思想,含有辯證的因素。他說:“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大一”是說整個空間大到無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說物質最小的單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內部。這和后期墨家一樣認為物質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物質粒子所構成。
他又說:“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這里是指事物本身的同一與差別的相對性。萬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質粒子構成,同樣基于“小一”,所以說“萬物畢同”;但是由“小一”構成的萬物形態千變萬化,在“大一”中所處的位置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以說“萬物畢異”。在萬物千變萬化的形態中,有“畢同”和“畢異”的“大同異”,也還有事物之間一般的同異,就是“小同異”。
什么是“大同”呢?比如馬;凡是屬于馬這一類動物都包括在內,這就是“大同”。其中黑馬、白馬、大馬、小馬等等又有差別,這叫著“小同”。馬這個大類概念與黑馬、白馬這些小類的概念有差別。如果從相同的方面看,這些都是馬。由此可以推知,萬物都有相同的一面。如果從不同的方面看,這些馬又都有差異。由此可以推知,萬物都有不同的一面。
惠施對事物的統一和差別的相互關系,有一定的認識。他認為事物都有相同之處,同時又有差別。事物的相同和差別是相對的,它們同處于統一體之中。然而惠施特別強調事物的差別是相對的,相同才是絕對的,所以他得出萬物“畢同”的結論。這樣就把相同的事物和不同的事物都抽象地統一起來。他更進一步推論出“泛愛萬物,天地一體”的結論。《呂氏春秋》說:“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這是對惠施“泛愛萬物,天地一體”的解釋,這已與莊子的“萬物皆一也”很接近了。但是,惠施的思想與莊子的相對主義還不能等同。莊子的相對主義否認事物之間有質的差別,實際上是否定了事物的客觀存在。惠施并沒有完全走入這樣的主觀主義。
惠施對“大同異”、“小同異”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分析,看到了其間的變異,只有這樣分析,才能如實反映客觀事物。而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又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主張“合同異”的惠施,也不可能絕對不講“離”。同樣道理,主張“離堅白”的公孫龍,也不可能絕對不講“合”。不過,惠施雖然講“離”,但最終還是講“合”,而公孫龍雖然講“合”,但最終還是講“離”。由此可見,惠施著重在概念外延的擴大,而公孫龍則著重在內涵的分離。這樣看來,“合同異”、“離堅白”兩派的名稱還是符合惠施、公孫龍思想實際的。
惠施的“歷物十事”研究的對象是物質世界。他善于對物質世界的本質和規律作出哲學的概括。在“名”、“實”關系上,他是從現實存在出發的,承認“實”是第一性的,而“名”是“實”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他和公孫龍的詭辯是有所區別的。
惠施有些命題是和后期墨家的爭論。后期墨家運用數學和物理學的常識,對物體的外表形式及其測算方式作了分析,下了定義。《墨子·經上》曾說:“厚,有所大。”認為有“厚”才能有體積,才能有物體的“大”。而惠施反駁說:“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認為物質粒子(“小一”)不累積成厚度,就沒有體積;但是物質粒子所構成平面的面積,是可以無限大的。
后期墨家曾經嚴格區分空間的“有窮”和“無窮”,《墨子·經說下》說:“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認為個別區域前不容一線之地,這是“有窮”;與此相反,空間無邊無際,這是“無窮”。而惠施反駁說,“南方無窮而有窮”,就是說南方盡管是無窮的,但是最后還是有終極的地方。
后期墨家認為“中”(中心點)到相對的兩邊的終點是“同長”的。《墨子·經上》說:“中,同長也。”而惠施反駁說:“我知天下之中央,燕(當時最北的諸侯國)之北,越(當時最南的諸侯國)之南是也。”因為空間無邊無際,無限大,到處都可以成為中心。
后期墨家認為同樣高度叫做“平”,《墨子·經上》說:“平,同高也。”而惠施反駁說:“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因為測量的人站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高低就不一樣。站在遠處看,天和地幾乎是接近的;站在山頂上的湖泊邊沿看,山和澤是平的。
惠施把一切事物看作處于變動之中,例如說:“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陽剛升到正中,同時就開始西斜了;一件東西剛生下來,同時又走向死亡了。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事物矛盾運動的辯證過程。但是他無條件地承認“亦彼亦此”,只講轉化而不講轉化的條件,這樣就否定了事物的質的相對穩定性,不免陷入到相對主義的泥坑中去。
莊惠之交
莊子有著曠達的心境,視富貴榮華有如敝屣。其高超之生活情趣,自然超離人群與社群。無怪乎在他眼中,“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莊子 天下》)(譯:認為天下人沉湎于物欲而不知覺醒,不能夠跟他們端莊不茍地討論問題)既然這樣,就只好“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了。像莊子這樣絕頂聰明的人,要想找到一兩個知己,確是不容易。平常能夠談得來的朋友,除了惠子之外,恐怕不會再有其他的人了。他們都好辯論,辯才犀利無比;他們亦很博學,對于探討知識有濃厚的熱誠。
惠子喜歡倚在樹底下高談闊論,疲倦的時候,就據琴而臥(“倚樹而吟,據槁梧而暝”),這種態度莊子是看不慣的,但他也常被惠子拉去梧桐樹下談談學問(“惠子之據梧也……”),或往田野上散步。一個歷史上最有名的辯論,便是在他們散步時引起的:
莊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橋上游玩。莊子說:“白鯈魚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閑自得,這是魚的快樂啊!”惠子問:“你不是魚,怎么知道魚是快樂的?”莊子回說:“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曉得魚的快樂。”惠子辯說:“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本來就不是魚,那么,你不知道魚的快樂,是可以肯定的。”莊子回說:“請把話題從頭說起吧!你說:‘你哪兒知道魚是快樂的’等等,就是你知道了我知道魚快樂而問我,那么我是在濠水的橋上知道魚的快樂的。”(《秋水》) 點評:莊子和老子的思想并成“老莊哲學”,足見莊子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之高。但是這個辯論中,莊子犯了一個重要的錯誤,惠子依據莊子的邏輯類比反駁之后,莊子才想起回到開頭的話題直接反駁,證明前面莊子已經犯了一個錯誤,莊子的反駁是無效的,即自己的反駁無效之后,莊子才想起回到開頭直接反駁。所以,綜合考量,這個辯論中,肯定不能說莊子勝了,莊子頂多和惠子打成平手。
莊子對于外界的認識,常帶著觀賞的態度。他往往將主觀的情意發揮到外物上,而產生移情同感的作用。然而,惠子則不同,他只站在分析的立場,來分析事理意義下的實在性。因此,他會很自然地懷疑到莊子的所謂“真”。
莊子與惠子的辯論,如果從“認知活動”方面來看,兩人的論說從未碰頭;如果從觀賞一件事物的美、悅、情這方面來看,則兩人所說的也不相干。而只在不同的立場與境界上,一個有所斷言(“知道魚是快樂的”),一個有所懷疑,(“你既然不是魚,那么你不知道魚的快樂,是很顯然的!”)他們在認知的態度上,便有顯著的不同;莊子偏于美學上的觀賞,惠子著重知識論的判斷。這不同的認知態度,是由于他們性格上的相異;莊子具有藝術家的風貌,惠子則帶有邏輯家的個性。
莊子與惠子,由于性格的差異導致了不同的基本立場,進而導致兩種對立的思路──一個超然物外,但又返回事物本身來觀賞其美;一個走向獨我論,即每個人無論如何不會知道第三者的心靈狀態。
莊子與惠子由于基本觀點的差異,在討論問題時,便經常互相抬杠,而挨捧子的,好像總是惠子。在《逍遙游》上,莊子笑惠子“拙于用大”;在《齊物論》上,批評他說:“并不是別人非明白不可的,而要強加于人,所以惠子就終身偏蔽于‘堅白論’”(“非所以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德充符》上也說惠子:“你勞費精力……自鳴得意于堅白之論。”這些批評,莊子都是站在自己的哲學觀點上,而他最大的用意,則在于借惠子來抒發己意。
另外《秋水》篇記載:惠子在梁國做宰相時,莊子去看他,謠言說莊子是來代替惠子的相位。惠子心里著慌,便派人在國都內搜索了莊子三天三夜。后來莊子去見惠子,對他講了一個寓言,把他的相位比喻貓頭鷹得著臭老鼠而自以為美。這故事恐怕是他的學生假托的,不過莊子與惠子,在現實生活上確實有很大的距離;惠子處于統治階層,免不了會染上官僚的氣息,這對于“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的莊子,當然是很鄙視的。據說惠子路過孟諸,身后從車百乘,聲勢煊赫,莊子見了,連自己所釣到的魚也嫌多而拋回水里去。( 《淮南子·齊俗訓》)
他們兩人,在現實生活上固然有距離,在學術觀念上也相對立,但在情誼上,惠子確是莊子生平惟一的契友。這從惠子死后,莊子的一節紀念詞上可以看出:
莊子送葬,經過惠子的墳墓,回頭對跟隨他的人說:“楚國郢人捏白士,鼻尖上濺到一滴如蠅翼般大的污泥,他請匠石替他削掉。匠石揮動斧頭,呼呼作響,隨手劈下去,把那小滴的泥點完全削除,而鼻子沒有受到絲毫損傷,郢人站著面不改色。宋元君聽說這件事,把匠石找來說:‘替我試試看。’匠石說:‘我以前能削,但是我的對手早已經死了!’自從先生去世,我沒有對手了,我沒有談論的對象了!”(《徐無鬼》)
惠子死后,莊子再也找不到可以對談的人了。在這短短的寓言中,流露出純厚真摯之情。能設出這個妙趣的寓言,來譬喻他和死者的友誼,如此神來之筆,非莊子莫能為之。
人物評價
惠施為戰國時代“名辯”思潮中的思想巨子,與公孫龍共同將名辯學說推向頂峰。并且為中國古代的邏輯空間的發展和認識。為對哲學形而上學的判斷提倡了一種方式方法。而且使對事物的本質的認識具有重要的貢獻。對老莊“無為”邏輯認識作出了解說的可能,甚至成為對刑法之術進行認識的邏輯前提。而且很多學術觀點都可以通過其基本原理進行推理。
惠施僅因莊子而得以傳其學問,現無法深悉其貌,惠施學問,莊子雖有微言,卻崇敬有加,惠施死后,莊子慨嘆道:“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